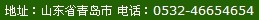|
[导读]在驻马店平原地区近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历史只有36年——36年前,几乎所有的村庄在几个小时之内消失殆尽。洪水毫无商量地改写了这些,洪水是被人们构筑的大坝拦起来的,后来,成为人类的水墓。 在36年后酷热的7月末,我们来到板桥水库。 在大坝复建纪念碑前,9岁的小姑娘王思念,手里拿着一本著名少儿文学作家马红鹰的书,旁边是自己家里摊在水泥路面上晒的小麦。 粉红色衣服的小女孩,安然地生活在大坝下面。复建的大坝依然连接着一南一北的两个山头,大坝显得结实而现代。 在大坝溃口处,一个当地警察在酷热的午后照例在村庄里巡逻,村子里除了老人,就是36年后的又一茬小孩。巡逻警察把没有空调的闷热汽车停在一片树荫下,打开门散热;在草丛里自在地小便之后,将脚伸到一个水管汩汩流水的小洞上,任哗哗的水流弄湿他的制服。 “你问‘75.8’吗?我们这代人没有几个知道。”警察有些难为情,笑着说。 是的,忘记的不仅仅是年轻的一代。包括他们的爷爷和父母们,也在忘记———前辈刻意忘记的是痛苦;年青一代,不经意间忘记的却是历史。 不仅是年青一代对“75.8”记忆缺失,就连属正史记载的当地县志,关于“75.8”的记载,也只有短短一小段文字,寥寥数语。巨大灾难在这里是那么轻描淡写。 被困水中的灾民。 把死去的孩子从妻子怀里蹬掉 河南省遂平县文城乡魏湾村的魏成栓和新婚妻子赵英被巨浪打散了———所幸,他们后来生子生女,已经有了第三代。共有28口的家族瞬间失去14口老老小小,而今重新兴旺起来———在魏湾没有谁家的房子比他们家的漂亮;而当年21岁的姑娘,变成了56岁的慈祥大妈。 8月8日凌晨,哥哥魏栓发现院子已经变成了大水坑,屋里的水也渐渐没过小腿肚。过了约半个小时,魏栓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,紧接着老屋内墙上的土块一直往下掉。“房子要塌,得跑。”魏栓赶紧招呼父母先出去,他一手拉着妻子,一手抱着小女儿向外走。水很快漫过了胸口,妻子拖着哭腔对他说:“你会水,你先走吧,看来我活不成了。”魏栓瞪了妻子一眼:“要死咱一块死。”刚出院子10多米远,魏栓回头看了一下,老屋已经坍塌了,很快消失在大水中。夫妻俩捞着一个东西死死地抱着。 “嫂子还抱着女儿,其实只有11个月大的女儿早就呛死了。嫂子依然死活不丢手,水大浪急,哥哥不敢松手啊,一松手也是死。哥哥只好把小女儿从妻子怀里蹬掉,任死去的孩子随波逐流”———三天后,魏栓和妻子回到家里,得知两个妹妹和两个孩子都没了。 赵英等人被困在了一座老房子里,那里聚集了近百人,大水已经向屋子里渗透了,“有人把被子往门上堵,想把水堵住。”当年的赵姑娘说,可是这时,房子塌了,房子是被水憋烂的,“百十口子,活下来的没有几个。”她和丈夫扒拉上了一个箔(河南农村高粱杆织成的席状物,很大,可以卷起来晒东西,也可以抹上泥巴当墙)。 57岁的陈志家,36年前是板桥水库水产队的职工,有幸赢得了那场“生死劫”,后调回薄山水库管理局灌区管理处,在那里,结婚,生子,在家庭困顿中提前退休。他大学毕业才30岁的女儿陈慧,身患尿毒症在床数年,已经花费了20多万的医疗费。 陈志家回忆起那个夜晚,他可能是幸存的板桥水库溃坝第一个亲历者,在巨大的水头上看到的一切:世界,就在他的面前眼睁睁地消失。“就这样飘着,这个时候能看见一些东西了,白花花的水啊。我在水头上,看到前面有村庄,有灯光,突然一下近了。人和哭喊声就在眼前,可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,过去之后,身后的水面太安静了。什么都没有了。” “当我能够抓着东西浮出水面的时候,我已经喝水喝得快撑死了。”他不知何时从船上落入了水里,另外六个同伴不知所踪。他拼命抓住了一件东西,似乎为船体的一块木板。“这个时候能听到周围的动静了,除了呜呜的水声,也听到了嘁哩喀喳的声音和人喊救命的声音,我不知道是在哪里。” 陈志家从水里冒出来有意识时,他回忆道:“雨一下子停了,天上有了星星。”这个景象在板桥水库水文站职工老黄那里得到印证,水冲下去了,雨住,天晴。 大水把一切连根拔起向高处转移的汝南灾民 36年后,56岁的“赵姑娘”在自家新起的大房子里回忆那时的惨象:“几天后,我们七八个人回到了村里,是按着记忆找回来的。”他们只能按照模糊的记忆寻找村庄,因为大水所到之处,房屋、庄稼、树木,一切“有根”的全被连根拔起,“留下白花花的生地,一棵庄稼都没有了。” 这是几乎所有经历大洪水冲击幸存下来的人回到村庄的记忆。 魏成栓家14口遇难的亲属中,只有奶奶的尸体找了回来。这个村庄的历史就此“从零”开始。因为,就连祖坟都被连根拔去了。“过去的东西,哪怕是一张相片,都找不到了。”村民李志国说。魏湾在年洪水中死去的千把号人,基本都没有坟头。埋什么呢?啥都没了。照片?唉,洪水扫得可干净了,现在有点连面目都记不清了。 不知过了多久,陈志家终于遇到了活着的人。“有些距离很近,可是谁也帮不了谁,水太快。不过大家能够互相说着话了。也看到一些冲得没力气的人‘出溜’一下子就落水里不见了。” 天快亮的时候,他问周边的人这是哪里,人们说这是阳丰乡。这个时候遇到了一棵树,树上已经有七八个人了,把他救上去了。 天亮时,赵英看到了一个大瓦房的房顶,喊上面的人,才知道冲到了铁路边的仁桥。魏湾村被冲得最远的一个人到了上蔡。 大部分从板桥水库被冲下来的人,未能活着翻越京广铁路,水浪形成的巨大落差,在翻越铁路时下沉入路沟,那里成为许多人的坟墓。“基本是几十个回来一个。”水后,铁路路沟里沉积下的尸体不计其数。一位从武汉方向来的参加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后来回忆:“铁路两旁的树枝,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”。 大水下去的时候,人们把陈志家放到门板上,他的腿受伤了,流了很多血,垂死的他被放在一个淤杂堆上。等他能歪斜着走路的时候,医疗队的人竟然从他睡过的淤杂堆里拉出来8个死人。“我就睡在这些肿胀得像牛一样的尸体堆上。”他蹒跚着走到阳丰公社卫生院,那短短的三里路上,成百具死尸散落在路旁。 魏湾村东面的赵庄,赵学正和媳妇、7岁的妮子坐在房顶上。大水先猛地灌进房子,接着房子被水往上一拱一提,就散架了。 他和女儿抱着房檩条,开始往下漂。碰到一棵树的时候,树把房架给撞散了。女儿就此失散了。他左右不了自己的生死了,心想妞这么小,肯定是回不来的了。 “我们在水头。从文城到阳丰,一路上,听到前面喊救命,接着没声音了。一路上都是这样,感觉很奇怪,所有的东西在眼前变没了,掏空了。心里说不出来的一个东西堵着。”他漂到了京广铁路边的张店村,女儿漂得更远,并经历了几次生死。“她这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能坐这样的船。” 赵学正的女儿失散后,又抓了一个箔,箔卡在了一棵树上,天亮的时候,树被水连根掘起来,女儿又漂下去。“漂到遂平莲花湖的时候,孩子在水里哭,嗨,一个晚上啊,7岁孩子坚持到天亮!”一个大麦秸垛上,上面趴了十几口子人,孩子一哭,上面赵庄一个叫春莲的看到了,救孩子上了麦秸垛。麦秸垛过铁路的时候,被大浪打散了,断了两截,赵的女儿坐在麦秸垛前面,冲出去活了。后面半截麦秸垛上的十几个人,就活两个。 赵英和丈夫等人活着回到了魏湾,可是,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回来,最多的是10岁以下的孩子,这是魏湾人最不能提的伤痛记忆。“10岁以下的小孩就活了几个。”当年开学的时候,一年级学生只有三个,高年级的也就剩下五六个学生了。学校都开不起来了。魏湾断了一代人。 大水冲走了一切,包括那里一代人的生命接力。赵学正和女儿回来了,多口人的村子,他们是活着的来口人中的两个。 坠入旋流不复此生 大水过后的村子 板桥水库底部高程为米,文城魏湾高程为米,遂平县城的高程为65米,县城东部的高程为50米。这是一个洪水可以绝对控制一切的坡度。 板桥水库控制流域面积平方公里,水库纵长8公里,平均宽4.45公里。下游遂平西起文城公社魏湾,东至常庄公社任庄,长达55公里,宽15公里,有平方公里的土地,直接属于其扇面攻击范围。大坝被水头撕裂的缺口很快成为多米的裂口。 巨量的库水,犹如一把切蛋糕的刀子,轻松地将裂口从坝顶向坝基切伸,从20多米高的坝顶,直到坝基根部,近十亿立方米的水,再也没有阻力。 奔涌而出的更大的水流,雷霆万钧,成扇面的水墙,向他们蓄谋已久的目标扑去:田野、树木、飞禽走兽,平原上大大小小小的村庄和人们。 板桥水库大坝高仅为25米,库容仅为5亿立方米,板桥水库最大溃坝流量达到立方米/秒。板桥水库的溃坝洪水冲到下游约四十公里处的遂平县城时,还有立方米/秒的洪峰流量。洪水波以立浪或涌波形式向下游急速推进,时速在30到50公里。 换句让人无法接受的话,这就是一架绞肉机和粉碎机。 按照溃水的速度,大约十分钟左右,第一个水头来到板桥水库下游沙河第十一道弯北岸洼地的魏湾。 又几分钟后,洪水来到毗邻魏湾的赵庄———这是一个更深的洼地,村子里最高的树的树梢,还没有周围的地面高。 接着是文城、阳丰、遂平县城、京广铁路…… 死神邪恶地选择了黑夜。从凌晨一时到水势平稳的早晨,这5个小时是驻马店地区最漆黑的5个小时。5个小时后,驻马店迎来了新的一天的光明。 赵英对洪水以前,她初嫁的村庄的记忆是:夏日里青纱帐密密实实,瓜熟蒂落的季节里总能尝到瓜果的甘甜与清香。可这一切,已被洪水滚滚带走。 就在板桥水库溃坝之际,它北偏西的石漫滩水库亦溃坝,同时,河南中部两座中型水库、58座小型水库相继溃决,近亿立方米(注,加上此前暴雨已经滞留在平原地区的均一米左右的积水)的洪水肆意横流。驻马店地区东西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,多万群众被洪水围困。倒塌房屋万间,冲走耕畜30.23万头,猪72万头。跨越驻马店境内的京广线铁路被冲毁公里,中断行车16天,影响运输46天,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。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溃坝惨剧。 浑浊的水面上,是成千上万具漂浮的人的尸体,大人,小孩,老人,妇女,激烈的水流将他们的衣服剥碎,他们赤裸着,回归自然状态,而更多的,则被掩埋在水下。数不清的家禽走兽,野生的,家养的,甚至包括脆弱的昆虫,几乎被悉数格杀。 沿途的黑暗中,“呼通”、“呼通”的房倒塌声,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的树被击断声响成一片,撞击声中,那些呼救的声音,没有机会发出下半句的声音。 人们直接被水呛死,或被水中的物件击中死亡,或被电线、铁丝缠绕勒死,或被吸入涵洞窒息而死,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,坠入旋流不复此生。 没有人,也没有神能更准确地俯瞰这个被碾碎的大地。 当时间磨平伤痕走过35年后,人们逐渐听到、看到、“回忆”到那真实一幕的情景: 洪水“所到之处,建筑、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。干流(指溃水主要冲击扇面)水面上,人头攒动,拼命挣扎、呼救。遇难人的尸体和猪、羊、牛、马、鸡、鸭等动物尸体,顺水漂流。石磙碾盘被冲下沟河,链轨拖拉机、重型机械车床等随水翻滚。遂平火车站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,铁轨被扭成麻花形……遂平县燃料公司五十吨级地下油罐被拔冲走八个,最远的冲到五十华里外的宿鸭湖水库。 洪水过后,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。河沟里、淤泥里,人畜尸体,横七竖八。” 年8月8日3时左右,峰头高达7米到10米的洪水兵临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城下。它轻松地越过遂平县城,在遂平县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记载:“全县23万人被冲走,人遇难。” 可是,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是一直存疑的,因为,仅文城公社的记载官方数字是:全公社3.6万人口中,有1.8万余人遇难。该公社魏湾大队沿河五个村子李湾、魏湾、梁湾、吴湾、赵湾,一字排开: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;该大队三小队口人中仅存96口,有7家人绝户。 百万生灵的炼狱 “我看到了水从西南方向冲过来。”文城南街,70来岁的邓玉成回忆35年前,他从遂平县城回到家看到的情景,35年后,这座曾经的古镇已无往昔的寨墙、古老的房屋,“所有这个地方的一切都是重建的。” 这位遂平县塑料厂的厂长兼支部书记,在漫天的大水就要冲来时,和家人、小孩儿来到寨墙边。这时,他的邻居邓茂的媳妇刚刚在水里早产,人们搀扶着产妇也走向了两三米高的寨墙。 邓玉成刚爬到寨墙上,洪水已经排山倒海般扑过来了。“我突然感觉西南赵楼方向有一道亮的东西,一种奇怪的呜呜的声音。等黄色的发亮的线近了,突然拐弯,接着‘呼咚’一声,赵楼就被水拍进去了,开始还听到赵楼的狗叫人哭,很乱,几秒钟,赵楼啥动静也没有了。哎呀,跟拍蚊子一样啊!” 寨墙上挤满了人,未来得及爬上的,已经被水卷走了。邓玉成让家人抱紧墙上的一棵树,等着天亮。“和等着刀落到脖子上头落地的感觉差不多。”那是寂静的等待,“文城安静得像是连蚊子都死了一样。鸦雀无声,怕人。” 大水顺着文城向东北方向奔去,沿着35年后的一条宽阔的公路,直扑遂平县城。大水过了上仓、罗李、阳丰……瞿阳镇、京广铁路、八里杨村……大水没有终点,它的终点是要汇入江河,汇入大海。 “水头过去了,水的声音也小了。水面上漂过来的人,还有零零星星哭喊。这些都是上游村子里的,说不定熟悉的朋友和亲戚,就从自个脚下的水里流过去了!”邓玉成和活着的人眼瞅着被大水冲走的人不能施救,这是洪水沿途所有逃生者的悲哀。 洪水过后的文城、诸市、阳丰等一带,所有残留的树木,趴在裸露的土地上,一律指着一个方向:西南到东北,这是板桥溃水惟一留下的证据。 8日凌晨2点,洪水已扑向了遂平县城。 洪水以每秒六米的速度滚滚东下,上游被冲断的水泥电线杆连着高压线,在洪水中直扑下游,拉直的电线犹如一把利剑,所到之处,房屋、树木、建筑物拦腰切断。有的人被电线切去了头,有的被斩断了腰,有的被击昏致残,几乎无一幸免。 遂平县招待所里停着一辆炮二师的军用吉普,几名战士把电台架在车顶上,轮流向外呼叫,但报话机里没有任何回声,洪水切断了县城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 中共驻马店地委第一书记在洪水来的前夜,还在郑州参加地市书记会议,在他心急如焚往驻马店赶时,大水已经冲断了路。他后来绕到周口、项城、新蔡、越过淮河、经淮滨、信阳,又转乘火车,多公里的路却绕行上千公里才辗转回到驻马店。 中共驻马店地委、地革委在想到向上级报告时,电讯中断,电报由驻马店军分区发往武汉军区,转到安徽合肥,再上报中央。 就在驻马店的告急电报辗转到达北京时,洪水的巨浪继续东进,在扫荡了上蔡、汝南之后,于8月9日深夜,洪水淹没了平舆县城。至此,板桥水库溃水,完成了对驻马店地区生灵肆无忌惮的涂炭。 可以查询到的档案资料显示,在那几天里:汝南,10万人被淹(指尚漂浮在水中),已救4万,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,要求急救;全县20万人脸浮肿;新蔡,30万人尚在堤上、房上、筏上,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,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;上蔡,60万人被水包围。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0人已把树叶吃光,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人6天7夜没有吃饭;平舆,40万人在水里…… 新蔡、平舆东部水仍上涨,全区万人在水中。 这是大水过后的怎样的一座炼狱?没有人见过这样一具棺材,见过这样的一座坟茔:几十亿立方米的水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埋葬了这一切。 逐渐回归的人们却找不到家在何处,他们要花费很长的时间,来找到自己的房舍依稀可能的地方。失散的人们,夫找妻、妻找夫、父找子、子找父、兄觅妹、弟觅姐……互相询问,东奔西跑。 几乎每个村庄,都失去了很多孩童叽叽喳喳和哭闹的声音:几个小时前,还是家庭希望的孩子们,就如小鸟一样去了天堂。一些村庄,十岁以下的孩子很少再回来———水,比他们脆弱的生命更坚硬。 腐尸遍野,夺命瘟疫 滔天洪水过后留下的,是一群群体力不支的人,饥饿、疾病、甚至传染性疾病,在大量尸体未能清理之前,瘟疫随时可能爆发,将有一批人不能逃脱第二波的劫难。 灾后第21天,恢复运转的遂平县革命委员会发出了“遂革发75(30)”号文件“关于当前防病治病的通知”。“由于灾后环境污染严重,人群抵抗力下降,乙脑、伤寒、疟疾等传染病日趋上升。”文件说,医院建立起来,加强疫情报告,就地隔离治疗传染病。 京广铁路以东,地势低洼,从西平到遂平、汝南、平舆、上蔡、新蔡洪水连成一片,在数百里的洪水中,人们被围困在房顶上、树杈上或河堤上,开始打捞些瓜果、玉米棒充饥,后来只能吃树叶、树皮。 中共驻马店地委组织了几艘机帆船,日夜不停地抢救群众,但数百万被浸泡的人怎能救完——— 水坑里、田埂边、桥洞中、到处都是死尸,横七竖八惨不忍睹,有的死尸倒悬在树上。卡在柴草堆里。埋尸队员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将尸体集中在一起,给赤裸的尸体裹上随手都可以拾到的破被子、烂床单和衣服,掩埋起来,在地上留起坟头。但尸体太多,有的已无法辨认,更无法挪动,只好在水坑里,路边上挖几锹土,就地掩埋。在车站,铁路两旁、车辆里,淤积了大量尸体,既无法挪动,又无法掩埋,只好浇上汽油点火烧掉。逐渐发臭变烂甚至产生毒素的人和动物的尸体,弥漫着人们说不清楚的雾气。 由于细菌的吞噬,天蒸地热,尸体正在可怕地威胁着无衣无食,体能消耗过大抵抗力越来越弱的存活者。大量蚊蝇滋生,树上的苍蝇结成辫,滚成团,压弯了树枝和高压线。医疗队宣读慰问电 逃难而生的陈志家被阳丰公社卫生院收治,那里已经挤满了病人。他是板桥水库的人,因此受到了格外关照。卫生院里,开始是受伤发炎的,后来是传染病发作的,每天都有人在死亡。由于病人接收太多,一座两层小楼由于住人太多而倒塌,又有很多人被砸死砸伤。 遂平县档案馆的文件记载:“灾后的遂平县腐尸遍野,苍蝇成群,外伤、肠炎、红眼病等发病人数达24万,前来救灾的北京、广州、上海和解放军等11个医疗队,共计人。9天时间里治疗人。” 如何去除瘟疫,消灭蚊蝇,治疗和预防疾病,遏制传染病和瘟疫的蔓延,遏制第二波可能比第一波更大的死亡悲剧,是摆在丧失部分机能的政府机器面前巨大的课题。 更为致命的是,在一片洪荒之中,本来就很薄弱的医疗系统陷入瘫痪:各县、医院和诊所房倒屋塌,药品器械不是被洪水卷走就是霉锈变质。 由于交通依然不畅,上述各县的发病数据相当不完善、精确、详细。流行性感冒、细菌性痢疾、传染性肝炎、疟疾、流行性乙脑、钩体病到处扩散。文件档案显示,据不完全统计,病人有.3万…… 现驻马店市档案馆藏资料显示:8月18日,平舆、上蔡、新蔡三县尚有88万人被水围,群众生活极困难,华陂公社5.6万人仍有2.16万人泡在水里,已病死21人;汝南发病32万。其中痢疾3.3万,伤寒人,肝炎人,感冒2.4万,疟疾人,肠炎8.1万,高烧1.8万,外伤5.5万,中毒人,红眼病7.5万,其他2.7万。8月20日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,病死者人。 从8月9日至22日,卫生部、解放军总后勤部、北京、湖北、河北、山西、武汉军区、广州军区、河南省军区及全国各地市的个医疗卫生部门,派出三千多名医务工作者先后抵达灾区。空军从9月1日至6日连续出动飞机架次,喷洒可湿性“六六六”粉吨,覆盖了宿鸭湖以西平方公里的地区。 炸开班台闸 魏成栓、赵英、李志国,那些活着的魏湾村民,在摸索着找到村庄遗骸时,已无一口可以充饥的粮食。 驻马店地委、地革委的求救电报最终到达了北京,8月9日晨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指示到达全国各地:河南地方的党政军民要集中力量抢险救灾,重点是救人;明天中午派慰问团到河南;要求各省向河南支援大批救援物资。 8月9日深夜,遂平县委召开了紧急的常委会,决定向全县发出安民通告。但广播没有了,电讯中断了,最后想到用大字报形式贴出去,可是,找遍整个县委机关却无一张纸墨,最后在招待所楼上翻到了红纸,洪水过后的第一份安民通告才发了出去。 灾后第四天,中共中央的慰问电到达河南,号召灾区人民向洪水灾害作顽强斗争。 灾后第五天,中央慰问团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的率领下,到达驻马店,纪登奎等人乘坐两架米-8直升机作了空中视察。 解放军以最快的速度向驻马店推进,海陆空立体地向灾区数百万人进行着当年力所能及的施救。空投粮食,成了解决饥饿的幸存者口粮的唯一办法。那些从天而降的食物有了一个称谓:天馍。 “那时的省会郑州,简直成了大饼、馒头的世界,都是发往灾区的救济食品。”河南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。 原驻马店地区档案馆馆长朱玉福当时在地区救灾办公室工作,奉命到省委报送材料时,看到大街小巷扯起了绳子,晾满了不计其数的大饼,忍不住热泪盈眶。 从灾难发生到年9月5日,从北京、广州、南京、兰州、济南、成都、武汉7大军区,和北京铁道兵司令部、北海舰队、东海舰队、河南省军区等赶赴驻马店灾区抗洪抢险的部队,诸兵种已达人。 灾后短短的几十个小时里,炎热的太阳,将数万平方公里的水面加热,几百万具人和动物的尸体开始肿胀发烂。 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班台水闸成了困住洪水东去的“拦路虎”,如果不打开班台水闸,洪水继续浸泡着数百万的民众,发病率将迅速上升。只有一个方案:炸掉班台闸。 陈惺,河南水利厅水利专家,参与了板桥水库的设计。南都记者试图寻找到这位历史的见证者,遗憾的是,河南省水利厅的人员传递出的消息说:陈惺已于去年辞世,带走了许多不能说的秘密。 史料记载,陪同纪登奎视察的正是陈惺,他们察看了京广线以东灾区,汝南、平舆、新蔡、上蔡和西平县的范围内见到的几乎是一片汪洋,5座县城和条条块块分布的高地如同散布在海中的岛屿。直升机飞行的高度仅50米,能清楚地看到每座“岛”上都密集着灾民。一些“岛”人多面积小,大量灾民不得不站在水里和爬在树上。 陈惺告诉视察的中央领导,必须炸开班台闸,加速行洪才能救百姓于洪水。8月14日凌晨,陈惺在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一再的嘱托下,与农林部长沙枫一起抵达北京,向李先念做了汇报。 李先念在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通话后,邓同意派出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舟桥部队,向陈惺在地图上指出的爆破位置进行炸坝任务。 随后,纪登奎做出决定,沙枫任指挥小组组长,陈惺、盖国英为成员,执行爆破任务。14日上午十点,沙枫、陈惺、盖国英等人已经几经辗转,从北京到达新蔡县,又换乘一艘柴油机船,驶向班台闸,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汇合。 此时,安徽阜阳地委书记正在班台闸的另一方,他被带到沙枫等人的指挥船上,沙枫下令他接受中央指令,转移下游群众。可是,他说,群众不愿转移,不同意炸坝……要与班台闸共存亡。 沙枫再次强调,中央命令一点都不能变动,必须炸坝。当日10点20分,10吨炸药爆破了班台闸,被束缚的洪水立即向下游泄去,被淹没了7天之久的驻马店,渐渐露出了地面。 买任意一款鞋子,雕牌洗洁精2元买回家。 赞赏 长按青少年白癜风的危害北京的权威白癜风专家
|
当前位置: 汝南县 >不该被泌阳,遂平,汝南人忘记的历史一
时间:2017/10/27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鲜为人知的大灾难1975年河南驻马店板桥
- 下一篇文章: 汝南老乡,原来我们的金铺镇大有来头